欢迎来到noYes游戏王国
网站导航
在上一篇文章中,小编为您详细介绍了关于《《最后的天子——午格》——别咬我兔耳朵》相关知识。本篇中小编将再为您讲解标题《定风波——高先生的故事》:遇雨独不觉一。
遇雨独不觉一
薄薄一层雪,太阳出来以后,就都化了。
"煤块"不知从哪里拱了一嘴泥,从下水道孔"哧溜"一下钻回院子里。尾巴梢居然一点儿没沾水。房檐上有晴光,照在几只"叽叽喳喳"乍开黑翅膀晾晒的花喜鹊头顶,是个好天。
我站在院子西北角台阶下,大(山西部分地区方言,指父亲)正一锹一锹在"搅煤糊糊"。厚厚的黄胶泥围起近两尺高的煤坑里,黄色的周围一会被带入黑坑里,一会儿又被带入一锹,在黑色的表面上划出一条艺术般流畅的黄线。这是我爱看的把戏。等到黄色被黑色完全吞没时,日头已经架在东南角的桑葚树梢。该吃饭了。
东厢房里白腾腾的,蒸气扑打着头顶上方发黄的窗棂。大哥国安半蹲半跪在起劲儿拉着风箱,四弟国盛在一边添柴火打下手。那大锅里是掺了糠的玉米面锅贴,我家桌上常见的主食。等大和我把脚上的泥收拾干净,饭也上桌了。
"强子,叫毛毛去。"哥的手在裤缝两边擦了擦,对我说。
国盛把能坐四个大人的长条凳子拉到靠墙的矮桌边去。
转身要去,大在桌子边坐下磕了下烟锅袋,说,"不用了,在你奶奶家吃。"
我看了一眼哥和国盛,走过去,挨着坐下来。
桌上是一碟豆叶子腌制的咸菜,撒了玉米面和一点盐巴的三大洋磁碗稀汤面糊,一碗端在大面前,两碗在我和国盛跟前,哥说:"先喝!"大推过来那碗:"谁喝完了让碗。锅里还有。"他的手伸向那发出熟悉粮食皮香味儿的、半黑瓦盆黑沙带黄冒热气的锅贴饼子。"煤块"毛茸茸的头拱到膝盖边来,我拍了它一下:"没规矩!"
"没规矩"这话是跟毛二萍学的,毛二萍是村东头教书先生毛驷攸家的二姑娘。年纪小作派不小,喜欢把狗崽子"煤块"叫做"小狗子",跟叫宫里的小太监似的。喜欢梳两把小抓髻,跟别人家随便绾的两细绺"狗串串"麻花辫不一样,还让她妈扎两条粉澄澄的绸子在两个脑勺子上。走到哪儿,两个脑勺子扎眼到哪儿。东垴上一晃西垴就瞭(看)着了。我们背后给她起个外号叫"气死一条街"。后来嫌叫着长,叫成"一条街"。
"一条街"上学堂。有一次给我们看她的课本,封皮三竖排字,她指着念:小学适用、新式初等国文读本、书局出版。
国盛眼尖,指着念的第三列问:"这里不对,毛先生不是这样念。"
一条街飞快地看了我们一眼,"你说?"
"这,我也数不出来。"国盛挠挠耳朵根,"不过,我见过毛先生教的,不是这样念法。"
"那你说,咋念的?你念,"
"这样,"国盛装模作样也指着课本,"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后面特意加重了语气。
"嗬,还一个字一个字,"一条街拿出她一贯的神气来,"我看你就是个睁眼瞎。"
毛毛在门后头闪出半个脑袋吐舌头,做鬼脸。
大哥拉着板车回来了,开始一小捆一小捆往下搬上面的豆秧,我呵斥毛毛:"搬凳子!"
都在院子里摘豆荚。
黄黄绿绿的黄豆秧铺满了小半个院落,毛毛拿着个大白洋磁碗,左右狗颠似地蹿,往里面讨半老不嫩黄绿的豆荚。晚上有一顿好吃了。我警告他:"不准跟去年一样,你吃了独食儿!在家煮!"说着转头跟国盛说:"看着盐巴。"
毛毛转头看看大哥,见大哥不做声儿,有点丧气。
二皮脸(骂人脸皮厚),我心里说。跟"一条街"一样,仗着有靠山。
二皮脸的靠山就是我们的奶奶。爷爷和奶奶跟二叔住新院,就在出门右拐过一条小河渠,三间靠荫沟岩、东南角茅房顶堆着黄柴草的窑洞就是。听奶奶说,白条石砌的长门洞里,塞着我们兄弟三个:我、国盛还有毛毛的胎发。那会大哥和二哥出生时,还没分家。分家应该是民国十四年,二哥出生后的事。奶奶炕上正对房梁吊着一个针线笸箩,笸箩里常藏着一两样好吃的:一包红薯干或者香甜的黄疙瘩(纯玉米面饼子),有时会有麻纸包的糖精。奶奶说她老了,克化不动饭食,二皮脸就成了常蹿那火炕的猫。
奶奶常常在摩挲猫蜷的毛毛时叹气,"我的毛毛最恓惶(方言,可怜),我的四个娃最恓惶。"
我知道,她又想起我的妈妈了。我没见过妈妈,毛毛出生那天她就死了。奶奶说,妈妈是憋了最后一口气生出的毛毛,那一口气救了毛毛的命。她的腿一蹬,毛毛就出来了。毛毛是裹着妈妈最后的体温出来的。
刚出生的毛毛不会哭,大概被大人们的叫喊吓坏了。奶奶冲上去,从后背狠拍了一下子,他才"哇"的一声哭出来。人都说,这样的孩子,命硬。
我看不出二皮脸哪里命硬,他除了长得佝偻猴似的不像我们能挺直腰,不像我们黑直硬的小辫儿长长的在后面搭着显精神,他那黄蓬蓬的一团编起来,没几根好搁捣(弄),在我眼里和"一条街"一样娇得不行。一条街爱干净,爱咋呼,人家有那资本。二皮脸不一样了,他是仗着奶奶才不把我们几个放在眼里,他还跟大撒娇,别看我大平时不爱说话不爱笑,黑塔神似的,二皮脸就敢不怕他。
我六岁就跟着下地干活。跟着爷爷去镇上石灰石厂,爷爷指着路边腰上系围布一脸黑胡茬的叔叔说,"强强将来做这个好不?"我一看,有风箱,地上有锉子和钻凳,我就知道是干啥的,抿上嘴不出声。爷爷拍拍我的颈。等会儿他给人装完石头又问:"长大跟爷爷装车行不?"我看着他认真地说,"等我长大你就死了。我不扛大铁锹,我将来要像毛先生那样,拿笔杆子!"
二皮脸今年数上六岁了,看看他都干点啥?穿开裆裤,一叉开老鹰抓小鸡时,两瓣屁股蛋跟两个脏蒜瓣似的。哪也抓爬,有一次上树,不知咋挂杨树杈上出溜不下来,吓得"哇哇"叫。大又不在,还是隔壁叔叔把他抱下来,一看***破了皮、流了血。当时吓得奶奶赶紧去"雲霄殿"给娘娘①烧了三张黄裱纸,祷告半天回来。可怕断了他的命根根。
和四五岁的女女小子们满街巷地窜;奶奶的炕上有他;"柳树清"捉鱼有他;打驴上磨盘有他;一听哪里有好吃的,十八里望风追,鬼催着就来了。好比现在。
奶奶说过,大忠臣,二奸臣,三鞭杆子(方言,脾气燥)四妖精(方言,精明,作妖),五能带(方言,鼻涕),六没相(娇惯得没样子),七的当家八拼命。意思生孩子是一个比一个聪明,到了后面也一个比一个没地产,所以老小得自己拼命。这道理放我们家就对了。
老五可不是个活化的能带虫吗?
释义:①娘娘,传说中保佑12周岁前小孩子免灾除难,健康长大的神,也叫奶奶。全国多地建有"娘娘庙"。用来祈福求子。每年三月三日是其生日。
定风波——高先生的故事(二)
(二)
高高扬起的秸杆
轻轻放下的秸杆
我打你了哟
我打你了哟
半夜院子里一阵鬼吼儿郎嚎的风声,我和国盛挤来挤去,裹一个被窝也不暖和。好不容易捱到天明,院子里尽落了一尺厚的白棉雪。
村里边,就是最冷的冬日也不兴睡懒觉。窗缝儿还压得严丝合缝得黑呢,隔壁的花脖子大公鸡就要哦哦地啼唱,等到人摸索着起来,窗户纸也就跟着透出丝亮儿来。但今天不同,被雪早早借一点天光就把人唤醒。
扫过雪,饭还早。婶婶把哥那床被子拿了过来,前几日和他们的一起拆洗过,掉出的棉絮重新给装了,开了的布头边也都细细地严实过,灰的黑的蓝的,长的圆的方的,看着像龙天庙里大和尚的百衲袈裟,重新变得新鲜起来。
奶奶打好了浆子,过来糊窗户,后面跟着毛毛,不过两步地的功夫,耳朵鼻子就冻得猴屁样通红。我和国盛已经剪好一对儿"鼠抬寿桃"大红窗花。就等着往上贴了。
老鼠上了窗户,扁担挂了寿桃,蝙蝠团成八只,家家户户糊完窗户,那窗花就跟春天的花大姐(方言,蝴蝶)押着夏天的阳坡颜(方言,阳光),白的光衬了红的彩,喜喜气气上了窗。于是南阁到北柏青山,东马家塄底到西荫沟,这红颜色高翻了低,低又翻了高,过了河渠,绕进胡同,不一会又蹿出巷子,直到一路喜气洋洋杀到各座老庙的戏台子上才算完。不过半天的功夫,立壁村翻了新。只剩下一股面浆子味萦绕飘荡在人声狗吠的空气里。
要过年了。
姥姥去年来时是二十九。那天我挨了打。
一早也是这个光景,太阳刚侧上个影在正堂,我在东厢打破一个碗。大二话不说把我臭揍一顿,嚎了半天奶奶才来。当然这不算奶奶偏心,她正忙活和二婶给我们一大家准备第二天的年夜饭,一年一顿的饺馅,饺皮是白面的。这年二叔在窑口上挣下余炭,拾弄了二两猪肉回来过年,可把婆媳俩高兴坏了。就在这快活的气氛蔓延家中的时候,我竟然摔了家里唯一的蓝花瓷碗,那是当年母亲的陪嫁物,另一个据奶奶说跟着母亲埋进了地里。碗碎成三片的那一刻,奶奶正和二婶往炕上搬两颗大白菜;我大动武的当口,她开始和案板上的大白菜还有葱蒜作起同样的斗争;案板剁得比谁家都热闹时,我嚎开了。
大一般是不开揍的,但揍起来也是最狠的。我记得一次国盛淘气,因为斗败嘴,把马家塄底二丫头家刚拿大粪水浇过的一分葱地拔了个七零八落。大一进门当即扔一柄锹过来开打,锹柄都在阶前磕断了,可见他的劲有多大。
奶奶搂住我,说等补碗的马麻子来了花一两个小钱补起来就好了。我一边哭,一边咬牙,二皮脸这个反叛,肯定是他告密,还没等我想好对词呢。我还气他的"特殊化",那次国盛挨打屁股的伤还没好,他就偷了家里最宝贵的盐粒,跑去二丫头家煮吃的。回来直接溜奶奶炕上去了,后来听说大在屁股上拍了两巴掌完事,没再追回赃物。
赃物是啥,就是我们兄弟几个藏起来准备煮的一白洋磁碗黄豆荚。
和去年一样,上午饭过了一袋烟的功夫,姥姥踮着三寸小脚拄着拐棍跨进了门槛。带来了黄花馍。她笑:今儿可是"年三十儿"了,做下不是(错事)也不用受罚的。确实,今年没三十儿,今天就是除夕了。
姥姥住隔壁西峪村,离我家没多远,过一个浅高的小山梁就是。那两年妈妈刚没的时候,姥姥常常过来,照应我们一家子。这两年身体不好,我们也有奶奶看,算是比那些没娘照应的孩子强多了。
放下东西,姥姥先去桑葚树下堆杂物的那间小耳房,那里有一个角落,用黄裱纸写着我妈妈的牌位。上了香,又给旁边红纸的牌位前,放一个红艳艳的大苹果,那是我的二哥。两个牌位前都没供照片。
二哥殁的时候不过两岁多一点,那时我妈已经怀上了我。有一天妈给二哥洗澡,发现儿子的腿根洇出细碎的红点子来,当时村子里出麻疹的孩子已经殁了好几个,都拿木头匣子钉住送到东山沟去了。那时,每到黄昏全村都盼着钉锅的来。我们这里管筛面的细筛子叫箩,一两年农闲的时候,村里来一个手工艺人,将一个个箍好的圆木框和一面面细网用小钉子装起来,再用特制的十字木头楔子固定好。这叫装箩。装箩的一走,往往就流行麻疹病,但是没有办法,大家就盼钉锅的来,只要钉锅的锤子一敲响,麻疹就敲跑了。"装箩来,钉锅走,没福气的白各悠(白来世上一趟)",老辈人都认命。
那一年钉锅的迟迟不来,病来得急,活活折磨了刚满两岁的二哥一个月,病情反反复复,红口小儿咿呀出声,营养不良加病痛折磨,越发显得小身子拱着大脑袋,最后那几天,脖子肿得赶上细面筛那么粗了,两只小手到处抓挠着,抓挠他唯一的依靠,抓挠着让他安心的那个人。
蒜水搓,姜水洗,做娘的心都给揉搓碎了。老天爷没给情面。该走的还是没留下,那年头哪家不折挫孩子呢?留不住的就是来讨债的,送要好发送,好好送债主走,以免他不甘心再来。二哥就这样不见了。
但妈妈没有留一张照片,不得不说在我们孩子的心里,留下了一大块洞似的感觉。那个洞总是化为幻想,在狠挨大打的时候,在和别的孩子斗败嘴的时候,在嫉妒毛毛的时候,幻化出不一样的形象来。
一天两顿饭,下午饭在后晌一接酉时,也就是隔壁花脖子上架回窝,太阳骑上东墙头时。姥姥不留下来吃,这时已经把家细细收拾完,要回去了。花馍摆在了贡桌上家谱前,那里还有插着香的三个黄馍。红纸裹着的圆木块里有麻油捻子,是准备一交年夜就给祖宗点上的。
临罢,姥姥嘱咐窑口刚回来的大哥,记得明早也给"立立"留糖水喝。大哥回,立立和妈妈的要另外留出半碗来。
那个碗,就是妈妈留下的蓝花磁碗,钉了9枚铜钉,像是庙里的和尚受完了戒。马麻子钉得严丝合缝,一点儿不漏,除了那疤,比家里任何碗都耐用。大却再不让我们用它,只留着年节上贡用一下。
编后语:关于《《定风波——高先生的故事》:遇雨独不觉一》关于知识就介绍到这里,希望本站内容能让您有所收获,如有疑问可跟帖留言,值班小编第一时间回复。 下一篇内容是有关《《贾晓峰的单人旅途》:第1章 毕业,分别,旅行,未知来电?(求收藏,求推荐)》,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进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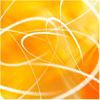


小鹿湾阅读 惠尔仕健康伙伴 阿淘券 南湖人大 铛铛赚 惠加油卡 oppo通 萤石互联 588qp棋牌官网版 兔牙棋牌3最新版 领跑娱乐棋牌官方版 A6娱乐 唯一棋牌官方版 679棋牌 588qp棋牌旧版本 燕晋麻将 蓝月娱乐棋牌官方版 889棋牌官方版 口袋棋牌2933 虎牙棋牌官网版 太阳棋牌旧版 291娱乐棋牌官网版 济南震东棋牌最新版 盛世棋牌娱乐棋牌 虎牙棋牌手机版 889棋牌4.0版本 88棋牌最新官网版 88棋牌2021最新版 291娱乐棋牌最新版 济南震东棋牌 济南震东棋牌正版官方版 济南震东棋牌旧版本 291娱乐棋牌官方版 口袋棋牌8399 口袋棋牌2020官网版 迷鹿棋牌老版本 东晓小学教师端 大悦盆底 CN酵素网 雀雀计步器 好工网劳务版 AR指南针 布朗新风系统 乐百家工具 moru相机 走考网校 天天省钱喵 体育指导员 易工店铺 影文艺 语音文字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