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noYes游戏王国
网站导航
在上一篇文章中,小编为您详细介绍了关于《《抬脚便是一个坑》——是风不是沙》相关知识。本篇中小编将再为您讲解标题《前辈的人生》: 艰贞的老太太。
第一章 艰贞的老太太
李宽,李俊、李海、李河四兄弟,在他们的父母李文奎夫妇的掌管下,开垦了几百亩土地,春种秋收,每年秋后打下的粮食,上缴了租子、官税后(那时的土地都是大城子王府的王爷管辖,谁种地都得按种地的亩数向大城子王府纳粮)还能养家糊口。在光绪四年(1878年)初春,李文奎夫妇二人得病相继去世,兄弟四人没有了主心骨,在一起就过不下去了,就商量着分家。
光绪四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经李宽、李俊、李海、李河四兄弟和来人李贵、于文财、胡廷珍等人的协商把家分开。我父亲的太爷是李俊,当时分得房身一处,房子几间,土地多少亩,树木牲畜等,现在还保存有分家单。(照片在45页)。
我听父亲讲,在老哥四个分家时,李宽、李海、李河那哥三个都有妻子儿女,就我父亲的太爷李俊,在他不到30岁的时候就没了妻子,就和他的儿子李士功爷俩。哥四个在一起过日子时,有人做饭,做衣服还好过些。这一分开家,就爷两个过日子不免有些困难。李俊拿到分家单后,看了看刚满十四岁的儿子,不觉落下泪来,对儿子说:“儿啊,分开家啦,爹也不会做饭,也不会做衣裳,我们爷俩就得冻死饿死呀。”李俊的三弟李海听他二哥这么一说觉得可怜,就说道:“二哥不必着急,我还有个会做饭会做衣服的,我就士荣一个儿子,现在还小,人口也不多,加上你们爷俩咱们才五口人,咱们两家暂时一起过吧。”李俊听他三弟这么一说,便随口答应道:“那敢情好啦,你可救了我们爷俩啦。”正好分家的房身,李俊和李海哥俩是前后院,李俊在前,李海在后,两家合成一家,前后院就成了一家了。
那一年李士功(我的老太爷)十四岁,李士荣才不满1岁,两家合一家还很好,李俊、李海哥两个和十四岁的李士功耕种着百十亩土地,地里的活一点也落不下。家里有李海的妻子做饭,做衣服,做鞋做袜、喂猪喂鸡等家务,连看着幼小的李士荣,家里家外都能照料,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光绪七年,(1881年)我的老太爷李士功已经长到17岁。李海就和他二哥李俊商量说:“士功已经17岁了,我看该给他说媳妇了。”李俊说:“我看还小点,再等等吧,现在咱家还不富裕,等明年或后年再说不迟。”李海说:“我看士功不小了,如果有合适的就该给他说啦,赶早不能赶晚,说上媳妇,结过来不也多个劳动力嘛,也能帮助他婶婶做点衣服什么的。”李俊听李海这么一说也觉得有道理,便说到:“可以是可以,但是哪有那么合适的姑娘啊。”李海说:“我听说上营子李家大院有一姑娘,很是能干,长得也很好,咱们可托人去说说看,如果说成了不是很好。”李俊听后便答应了。
当时上营子李家大院也算是一个大户人家,他们也是祖居山东,和我老祖宗李皋差不多一年搬迁过来的,家中也是兄弟几个在一起过,全家20多口人,房屋20几间,用土墙围城一个大院,所以叫李家大院。
因为都是上下营子住着,相距不足一公里,山上的庄稼地都是互相挨着,有的都是垄挨垄,所以互相都认识。
有一天,李海和李士功在东洼铲地,正好李家大院的李生(化名)和他的儿子李天明也在东洼铲地,相隔不远,铲地铲累啦,就坐在地头休息,看见李生爷两个也铲到地头,李海就故意的打招呼说:“老李大哥,累了吧,过来抽袋烟吧。”李生答道:“抽袋烟就抽袋烟。”便放下锄头和李天明走到李海面前坐下说话。李海从腰间掏出烟荷包递给李生,李生也从腰间拿出烟袋,装上一锅烟便吧嗒着抽起来。这时李海便问起李家大院姑娘的事情,李天明嘴快,见李海一问就答道:“那就是我的亲妹妹。”李海一听很是惊讶,便面对李生说:“闹了半天是大哥您的女儿啊,我听说你这个姑娘可是个好姑娘,又聪明又能干,咱们两家结个亲,你看好不好?”李生见李海这么一说便问道:“不知你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何人?”李海回过头来看了看李士功,见李士功低着头,脸都红啦,并没有及时回答李生的问话。便对李士功说:“士功过来和你大爷说话。”李士功见他三叔招呼他,便站起来,大大方方走到李生面前,先问了一声大爷好,便站到李海身边。李生抬头一看李士功这小伙子,不胖不瘦,中等身材,虽然整天在地里干活,晒得有点黑,但看上去很精神,也很标致。也就知道李海的用意了,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李士功答道:“我叫李士功”“多大年龄?”李生又问,李士功答道:“我今年17岁啦。”李生又问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李士功都对答如流。这李生不看则罢,一看便喜欢上这小伙子了。这也是缘分吧。但是李生还是留了个心眼,没有及时表露出来,便转过头去对李海说道:“你说的就是这个小伙子吧?”“正是,老哥哥你看怎样?”李海直言不讳地答道。李生又瞅了瞅李士功,见李士功低着头,脸色还有点害羞的样子,更觉得这小伙子很体面,便对李海说道:“等等吧,我回家和我老伴,女儿商量商量再说。”李海说道:“好吧,我就等候佳音了。”双方又说了些客套话,便各自铲地去了。
到了中午,李海和李士功回到家中,李海便把上午的事情对李俊详细说了一遍,李海说:“看李生的样子是同意了这门亲事,但他还要和他老伴商量商量。”李俊说:“那是必然的,咱们也得做点准备。”李海说:“我看咱们得抓紧时间,免得夜长梦多。”李俊点了点头,便商量着怎么来办此事才好。
再说这李生父子铲地到了中午回到家中,老爷子就把上午的事情和他老伴说了,他老伴听说要给女儿找婆家,从心里还是有些舍不得。因为他的女儿近二年帮她做了不少的活,无论是做鞋,做衣服、洗衣做饭样样精通,女儿真的一走她可要多受累了。但听说给她女儿介绍的女婿是下营子李俊的儿子李士功,不觉心中一动,就说到:“我也曾听说过李俊有个儿子很不错,你今天看见了,到底怎样?”李生说:“我早就见着过,但没太注意,今天仔细打量那小伙子还真挺好,说话也非常有礼貌,很有教养,很懂人工之礼,长得也不丑,身体也很健康,我女儿要是找一个这样的女婿就算很好了。”李老太太听了李生的话便说道:“好是好,女儿走了。我可就缺手了,家里的活谁替我干啊。”说完不免眼圈红了。李生看见老伴这样,忙劝道:“现在不过刚一提亲,就是订了亲我们暂时也不能让他们结婚,也得等明年或后年再让她们结婚,你犯的什么愁呢。”李生老伴听了便点了点头。
话分两头,再说这李俊,李海哥两个经商议,第二天中午,就把后院的李贵请来,炒了几个菜,在酒桌上便把请李贵的意思说了,李贵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一听说让他给侄儿李士功当个介绍人,到上营子李家大院提亲,便一口答应。
因为李生和他老伴都已经同意了这门亲事,所以李贵到他家说媒,真像《花为梅》中的阮妈妈说的那样“黏米面包饺子,一捏就成”便商定了良辰吉日两家就订了亲。
光绪九年(1883年)的夏天,也就是老太爷李士功定亲的第三年老太爷和老太太结了婚。
老太太和老太爷结婚后,全家人的衣服,鞋、被褥都是她做,和老太爷的感情非常好,她又聪明又能干,过日子方面还有计划,不但洗衣做饭,喂猪喂鸭等家务安排的井井有条,还能帮助老太爷计划哪块地种什么庄稼,上多少农家肥,什么时间干啥农活,都安排的头头是道,而且种什么得什么,收CD很好。不但做家务,夏天还上山间苗除草。结婚后二年小日子就大有好转,李俊、李海和老太爷都很佩服,所以结婚的第三年就让老太太当家,主持家里的一切事物。
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正月,老太太生下我的爷爷李春友。当年的三月份我们这个地区闹瘟疫,李海的妻子因染瘟疫去世,不几天李海也被传染了,他发烧、咳嗽、吃不下东西,几天就撂炕了,(按现在说就是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全家人都很着急。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太差了,根本没有什么医院卫生所,整个毛家窝铺就是老太太的娘家叔叔是看病先生。那时又没有西药,全靠中草药,当时对瘟疫是什么病也不了解,一说得了瘟疫都吓得不得了,不相干的人都躲得远远的,就是看病先生都不愿意给看病。老太太亲自回娘家请她叔叔,好说歹说她叔叔才不得不来。
李老先生来到李海的床前,让李海把手伸出来,他一摸脉竟吓了一跳,脉搏跳的特别快,再一摸脑门烫的不行,那时也没有体温计,可能高烧已经烧到40多度,李老先生便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就开了些:双花、连翘、苍术、陈皮、茯苓、桔梗、黄连、板蓝根、半夏、薄荷、大青叶、蒲公英、葛根、甘草等清热解毒去火的药,便急忙走出家门,老太太紧跟其后问道:“叔叔,你看我三叔的病怎样?能治好吗?”李老先生摇了摇头说:“不好说,治治看吧,病的非常严重。”把药方递到老太太手中又说:“你到我们药铺多抓几付药,让他吃吃看,他得的是传染病,我也不能再来给他看病啦,你也要小心,看他的病情什么样,你随时到我那跟我讲,如果有好转,我就再给他调方下药,如果没有好转就快给他准备后事吧。”说完便急匆匆的走了。
老太太急忙让老太爷去把药抓来,老太太亲自煎好,给李海吃上。连吃了几付药后,还别说,病情还真有点好转,全家人都很高兴。但过了几日,李海又高烧了。老太太急忙回娘家找她叔叔。可她叔叔这次说什么也没有来,对老太太说:“他的这种病就怕反复,一反复十有八九不行了,我去也没有用,我再开几付药给他吃吃看,如果吃着管用可继续吃,如果吃着不管用就不用再吃了,快为他准备后事吧。”老太太一听心凉半截,便急忙抓上药三步并作两步,急忙回到家中,把药煎好给李海吃上。但这次吃了药病情也没有好转,到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一天一大早,老太爷和老太太刚起床,李士荣就急急忙忙跑过来说:“二哥、二嫂你们快去看看吧,我爹他喘不上气来了,让我叫你们快点去呢。”老太太和老太爷一听,马上跑了过去,一进屋看见李海在炕上躺着,张着嘴大口大口的喘气。李海见老太太、老太爷进得屋来,强打精神用手指了指炕沿,意思是让老太太到跟前来,老太太急忙走到他的跟前,李海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侄媳妇啊,三叔快不行了,士荣年纪还小,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了,你千万把他抚养成人,给我留下这一后代根啊。”老太太见他这么一说也落下泪来,说道:“三叔您放宽心,我一定好好对待士荣弟,您要好好的养病不要多想。”李海含着泪点了点头。当天上午李海就因病去世,享年40岁。
李士荣的母亲去世不到俩月,李海又去世了,全家人都陷入悲痛之中。李士荣哭的死去活来,老太爷和老太太也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死去的再也活不了啦,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啊,老太爷和老太太张罗着请木匠,买木料,打了一口棺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也前来帮忙,在家放了三天,埋葬了李海。
李海夫妻从得病去世前后不到三个月,失去了两位亲人,又花去了近二年好不容易积攒下的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外债。李士荣那年才九岁。他的父母全没了,也不能自己在后院住了,老太太就让李士荣从后院搬过来和老祖宗李俊住在一起。老太太心眼好,对李士荣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的是无微不至。
当时正是夏季,地里的庄稼正是该除草、间苗的时候,一下子失去了两个劳动力,近百亩的庄稼怎么能忙的过来。老太太就借了点钱,买了一头毛驴,又请来木匠做了一个耘锄,让老太爷耘地,老太太领着九岁的李士荣上山拔苗,老祖宗李俊在家看门看着才几个月大的爷爷李春友。就这样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干了一夏天,庄稼长的比别人的都强,到秋天收成还算可以,打的粮食留下自己一年的口粮还还了不少外债。老太太就是这么一个又能吃苦受累又能治理家务,敢想敢干勇于担当的女强人。
就这样老太太和老太爷一家又辛辛苦苦过了几年。老太太又生下二爷爷李春生,老爷爷李春永,姑奶奶(不知名字)。我父亲听我奶奶说老太太真是个铁人,就是在生小孩坐月子时都不歇着,总是给一家人缝缝补补、洗衣做饭、喂猪喂鸡。出了月子就帮老太爷干这干那。白天和老太爷上山干活,晚上点着麻油灯做衣服,做鞋,做被褥等一时不闲。
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全家人已是八口人了,当年老祖宗53岁,老太爷李士功30岁,老太太29岁,李士荣17岁,爷爷李春友8岁,二爷爷李春生6岁,姑奶奶3岁,老爷爷李春永才一生日。老天又降下大祸,老太爷李士功因劳累成疾,又遇伤寒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年仅30岁。
老太爷的去世,让全家人都感到像天塌一样,老太太哭的死去活来,边哭边说:“老天爷呀,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啊,我们老的老小的小让我怎么过呀,你一闭眼撒手去了,也让我随你一起去吧,老天爷啊。”老太太哭的是天昏地暗,左邻右舍的人都掉下泪来,老祖爷子李俊也是悲痛欲绝。一家当户的父老乡亲都前来相劝,并且都上前帮忙做这做那,老太太的娘家亲朋也来帮忙。老太太的娘家哥哥李天明是个明白人,家中过得也很好,他见老太太家遇上这么大的事也前来帮忙,帮助买棺木,买伺候亲朋的伙食,又请来失亡会(当地的民间丧事鼓乐队)。折腾了三天,把老太爷埋葬了。
老太爷的去世对老太太的打击太大了,她整天以泪洗面,茶不思饭不想,几天的功夫人就瘦了一大圈。老祖爷子李俊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在背地里偷偷落泪。但他毕竟是个久经风霜的男人,便走到儿媳房间劝道:“儿媳啊,人死不能复生,看在几个孩子的份上,我们还得振作起来,好好活着啊,你可不能再倒下呀,你要是再倒下了,我和几个孩子也就没命啦,爸爸求你啦。”老太太见老祖爷子这样一说,心如刀绞,眼泪刷刷的落了下来,他瞅了瞅几个可怜的孩子,又看了看站在地上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公爹,心里想到:“对呀,我整天这样哭哭啼啼,能解决什么呢,孩子们还小,孩子他爹临终时嘱咐我的话,我都忘了吗?他让我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千万要把孩子带大,抚养成人。这是他临终的嘱托呀!他那语重心长的话我怎么就忘了呢。”想到这里,又看了看站在地上老泪纵横的公爹,擦了擦眼泪,便把心一横说道:“爸爸说的对,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把孩子都拉扯成人,您就放心吧!”老祖爷子这才点了点头,眼含热泪回到自己的房中。
老太太真是个钢铁之人,她那么的顽强、坚韧、纯洁、无私,她擦干了眼泪,又重新振作起来,不知疲倦地为这个家,为这几个孩子操劳着。
可想而知,在那经济落后的年代,一个农村妇女,在上有年过半百的老人,下有四个不懂事的孩子,失去了丈夫,是多么难过的日子啊。可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老太太硬是撑起了这个家。
又过了五、六年,老太太看李士荣也20多岁了,就托人给他说媳妇,但李世荣特老实,提了几个人家都嫌他笨,都没成。老太太觉得不给李士荣说上媳妇也对不起死去的三叔公公,特别想起李海临死前的嘱托,更是把老太太急得不行,就千方百计的到处托人给李世荣提亲,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为李士荣娶上了媳妇结了婚。也给家里增加了劳力。
李士荣结婚后,刚开始在一起生活还可以,慢慢的李士荣媳妇觉得他们就两个大人,都是劳动力,而老太太这边人口多,老的老小的小,总觉得有些吃亏,不免就有些不愉快的表情流露出来,老太太是何等样人,能看不出来吗?
有一天老太太把老祖爷子和李士荣叫到一起,对李士荣说:“士荣啊,嫂子也给你娶上媳妇成了家,我这边孩子多,在一起过、你们两口子跟着受累,咱们分开过吧!”李士荣一听嫂子这话,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背地里他媳妇经常和他说三道四,但毕竟这几年嫂子待自己不薄,发送了自己两个老的,把自己从小拉扯大,又给自己娶上媳妇成了家。媳妇虽然有些看法,但大面上也得过得去。今天听嫂子说要分家,总觉得过意不去,便说道:“嫂子说的哪里话,我小的时候,你不是照样照顾我吗?没有嫂子你哪有我的今天啊,侄儿们还小,我二大爷岁数又那么大啦,分家以后你们怎么过呀,还是别分吧!”老太太坚持说:“咱们分开吧,早分比晚分强,现在我们还很和睦,分开后,你们小两口的日子要好过些,也免得在一起时间长了,哪能勺子不碰锅沿的,等闹了意见再分家就不好啦。”老太太就是有这么宁天下人负我,毋我负天下人的精神,宁可自己多吃苦,绝不让别人跟着受连累。李士荣见老太太这么坚决,也觉得老太太说的有些道理,不分家自己的媳妇跟嫂子也不会长期过。想到这便说道:“那我就听嫂子的,分开家后,嫂子这边有什么活我们照样来帮忙,嫂子你尽管放心。”就这样找来会写字的先生于光志和来人李天明、李天增、李天忠、李士春、李士福、李士有、李士存、孙希珍等,在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十一月十六(1907年)老太太和李士荣分开了家。(现在还有分家单,照片在45页。)
家也好分,老祖宗李宽、李俊、李海、李河哥四个分家时所分的房子、土地、房身、树木等固定资产,谁家分的还是谁家的,就是些铁铣、镐头、木犁等用具分吧分吧,一头牛分给李士荣,老太太分了两头毛驴,有一辆破马车,(旧社会连轴转的木质马车)两家合用,粮食按人口分,李士荣人口少,又都是大人,老太太多给了他们几斗粮食,又找上来人,写了分家单就把家分开了。
分开家以后,老太太就带领我爷爷、二爷爷、老爷爷、姑奶奶这四个孩子和近60岁的老祖宗(那个年代60岁的人就觉得很老很老的)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拼搏。老太太还教育孩子从小就热爱劳动,不怕吃苦受累。每个孩子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春种时能扶犁的扶犁,能播种的播种,能捋粪的捋粪。姑奶奶才十来岁就跟着打簸梭。夏锄时祖爷爷和爷爷套上耘锄耘地,老太太领着二爷爷和姑奶奶间苗,秋收时,祖爷爷和老太太带领几个孩子起早贪黑把庄稼割倒捆好,就和李士荣搭伙一起往回拉。因为老太太这边没有会赶车的,爷爷和二爷爷跟着装卸车,套上李士荣家的牛,和老太太家的毛驴拉车。就这样春种秋收,一年一年苦干苦熬,终于熬到爷爷、二爷爷、老爷爷、姑奶奶四个孩子长大成人,老太太也操劳的累弯了腰,白了头。刚刚40多岁的老太太那沧桑的脸上就爬满了皱纹。
会有人要问,老太太29岁就没了丈夫,为什么没有再嫁人呢?自己带着孩子过日子多苦啊?听我父亲说过,老太爷刚去世的时候也有人打老太太的主意,托人来说老太太,但都被老太太拒绝了。老太太斩钉截铁的对来人说:“我活着是老李家的人,死是老李家的鬼,我这一辈子就他李士功一个丈夫,他虽然死了,但我有四个儿女陪伴,我一定把他们拉扯成人,我永不再嫁,让他们就死了那份心吧!”从那以后再没人敢上门提亲。
老太太就是这么一个贞烈、纯洁、顽强、坚韧的人。虽然老太爷和老太太结婚才生活了刚满十年,但他们夫妻二人的恩爱感情是很深厚的。就是老太爷死后的每一个春节,老太太都用黄表纸,让老先生写个牌位,让三个儿子到墓地请年,供奉在屋子的正堂,一日三餐前,首先为老太爷烧香烧纸,让几个孩子给他父亲磕头。并且告诉几个儿女永远也不能忘记自己的爹爹。
老太太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她那种纯洁、顽强、坚韧的品德,不怕吃苦受累的精神,永远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值得我们发扬和传承。
老太太拉扯着几个儿女苦干苦熬,过了十几年终于我爷爷、二爷爷、老爷爷、姑奶奶都长大了,在老太太的教育下,几个孩子都勤劳能干,能吃苦受累,但都老实忠厚,在那黑暗的社会不免受土豪、恶霸、地主的欺负。
父亲听我爷爷告诉,有一年秋天,我们家东洼有几亩高粱成熟了,我爷爷和两个弟弟去割了一天半,割倒后下午哥三个又去把割倒的高粱捆好,码成垛,准备第二天拉回。等第二天爷爷和二爷爷赶着车到地里一看,头一天割倒的高粱一颗也没有了,地上还有车印,看来是用大车拉走的。爷爷和二爷爷就顺着车印找,一直找到本村老于家的场院,看见那些高粱就在他们场院垛着。但是爷爷和老爷爷都是老实人,也没敢吭声。回家和老太太说了,老太太一听非常生气,但想了想对爷爷说:“这事你去找你大舅去吧,让他出面来找那于老财主,我们去找他肯定不会承认,你马上就去找你舅舅让他快点来。”爷爷一路小跑,到了他舅舅家。舅舅家是好大的院子,四周都是三米多高的围墙,黑漆木门,门里拴着一条大黑狗。爷爷跑到门前叫门,院里伙计问道:“谁呀?”爷爷答道:“我是下营子李春友。”因为是亲戚,爷爷也经常到舅舅家串门,都熟悉,伙计听了便把门打开,爷爷急忙问道:“我舅舅在家吗?”“在家,就在上房”伙计边说边指了指正房的东间屋,爷爷便急匆匆进了屋,见他舅舅李天明正在炕上坐着抽烟。李天明见外甥这么早急匆匆跑来便知有事,便问道:“这么早你来有事吧?”爷爷就把丢高粱之事向舅舅说了一遍。李天明听后问道:“你们看清楚了吗?可别弄错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爷爷说:“千真万确,我们顺着车印一直找到他家场院,我们的高粱就在他们场院垛着呢,一点都错不了。”李天明是何等人物,自幼跟着李老先生念书,跑过买卖,走南闯北,什么世面没见过,什么样的事都遇到过。家中又有钱又有粮,上下营子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听爷爷一说心中大怒便说道:“外甥不必着急,舅舅去找他便是。”说着就穿戴整齐,手提马鞭,背上背着个粪筐直奔老于家而来。
老于头是个土财主,家里有200多亩土地,雇着长工,有钱有粮,家住一个大院,五间正房瓦着小瓦,一个大门洞,他家院外就是他家场院。李天明在爷爷的指引下,看了看车印,又顺着场院门向里看见一垛高粱整齐地垛在墙根。李天明指了指那垛高粱说:“就是那些高粱?”爷爷点点头说:“正是”李天明确定了此事后,便走到于老财门前,用粪叉杆“铛、铛、铛”敲了三声大门。这时于老财正坐在炕上喝酒,听见有人敲门,就打发伙计去开门。把门打开后,于老头顺着窗的猫道(过去都是用毛头纸糊的窗户,下边一个角上留出家猫走的通道,边上粘块能掀开的布帘)向外观看,看见是李天明怒气冲冲,手拿马鞭闯进门来,于老财一见心中害怕,慌忙下地迎出门来,皮笑肉不笑的问道:“兄弟怎么这么闲在,今早来我家串门?”李天明瞅了瞅于老财没好气地反问道:“你不知道我来干啥吗?”于老头这时已明白李天明的来意。便装作镇定的样子,说道:“兄弟说哪里话,你来做啥我哪能知道呢。”“你真得不知?”李天明用犀利的目光瞅着于老财说。“不知道啊。”于老财这时心虚的说话都有些打颤。李天明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于老财的脸,便又问道:“我外甥东洼有块高粱,昨天三个外甥割倒啦,昨天夜里让你给拉来啦?”于老财一看瞒不住啦,假装糊涂,便结结巴巴的说道:“是吗?今天早晨我让伙计们去地里拉我们的高粱,莫不是拉差了吧。”随后便把伙计们找来,挤眉弄眼的说:“我让你们今早去拉庄稼是不是拉错了?”伙计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说什么,于老财怕事情闹大,忙说:“看来准是拉错了,都不支声吗,既然是拉错啦,快去告诉李春友他们把高粱拉回去,这是咋说的,天明弟不要生气,这也是伙计们黑灯瞎火看不清拉错了,我让李春友他们拉回去就是了。请兄弟到屋里坐,喝点水,抽袋烟。”李天明见于老财认了帐,但谎称是拉错了,也不好再说什么。便冷笑一声说道:“既然是拉错了,那就算了,以后可得注意,不要在干这种事情!”“那是、那是。”于老财点头哈腰地说。李天明见于老财这付德兴,变扭头出了他家大门。
李天明来到老太太家,就告诉爷爷去把高粱拉回来。老太太对李天明说:“全靠哥哥啦,要不叫哥哥你的面子。他于老财是不会承认的。”李天明说:“妹妹不要担心,以后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就去找我,有哥哥在谁也不敢欺负你们。这于老财真不是个东西,你们娘几个过到今天多不容易呀,他还敢欺负你们。告诉孩子们不要怕,什么事有我呢!”“是,是”老太太满口答应。便做熟了饭,又炒了两个菜,伺候李天明吃了早饭。爷爷和二爷爷套上车到于老财的场院把高粱拉了回来。这都是爷爷年轻时发生的事。
自从于老财偷老太太家的高粱被李天明给要回来那天起,全村人对老太太和爷爷、二爷爷都更另眼看待,觉得这李家有亲戚给撑腰,所以从那时起就没人再敢欺负爷爷和老太太了。
在老太太的管理下,再加上爷爷、二爷爷、老爷爷哥三个的苦干,几年来小日子过的越来越红火。每年秋收下来不但够吃够用,还能有所剩余,在加上老太太的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就积攒下几石粮食。
上书说了老太太的娘家哥哥李天明是个会做买卖的人。他家里也有钱有粮,春天青荒不接的时候他就把剩余的粮借出去,到秋天下来把粮食再收回来,一年下来也能赚点利。老太太就回娘家找李天明说我家有几石余粮,让他哥哥李天明放出去,一来可以赚点利,二来也可以陈换新,李天明就答应了。
爷爷和二爷爷就套上车给李天明送去一车,大概一石多点,李天明说:“不用往我这送,谁要借粮,我就打发他去你家拿就行了,送这一车就撂这吧。”
就这样大概一春一夏的功夫,李天明从老太太家给借出七石多高粱。这七石多高粱就一年滚一年的在李天明家滚了三年,也不知道赚了多少,老太太就听从她哥哥的。这一年秋天,老太太去哥哥家想问一问粮食的事,李天明说“粮食就在这放着吧,没不了,咋也能赚点,怎么也比你在家存着强。”老太太也相信自己的哥哥,账也没算就回家了。
可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冬天他的哥哥李天明突然得急病去世了。他娘家侄子给老太太送去信,老太太、爷爷等急忙去他家帮忙。忙活了三四天把李天明埋葬。等亲朋好友都走了以后,老太太就问她几个侄儿说:“你爸没死之前向你们交代没有,我们在你爹手里存放的高粱,他说没说过,现在是在家存着呢,还是都借出去了,如果借出去了都借给谁了,我好到秋天和他们要。”几个侄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说不知道。老太太又去问几个侄媳妇,也都说不知道。老太太一听心都凉了,经手的死了,剩下的都说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和几个侄儿说:“你爹活着的时候,我这几年在你爹手里存了七石高粱,他给我借出去,还能赚些利,你们也看见来,现在你爹突然去世,你们又都说不知道,我觉得这三年来也赚个一石两石的粮食,赚的粮我就不要了,把我那七石高粱本给我就行啦。”他的侄儿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管。把老太太气的不行,但和他们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生气站起身说道:“你们几个小兔崽子,给不给我你们看着办吧!”说完愤愤的回到家中。
再说老太太走后,她娘家几个侄子就商量着分家。几个侄媳妇各有各的心眼,该拿的拿,藏的藏,偷的偷,等到真正分家时,个别的媳妇的腰包都满了。把大面上的东西都分完后,老二媳妇和老三媳妇就问她大嫂,那咱爹柜里的几个大包袱快拿出来分分吧,老大媳妇一听眼珠一转说:“哪还有什么大包袱啊,都让下营子大姑(指老太太)拿去啦”老二媳妇和老三媳妇一听都很生气。
过几天老太太又回娘家问侄子们粮食的事,几个侄媳妇不但不承认粮食的事,还硬说老太太把她爹柜里的大包袱拿去啦,把老太太气的和几个侄儿侄媳妇吵了一架,气得她浑身发抖,但也说不出什么甜酸来,带着一肚子的气回到家中。但怎么想也消不了这口气,就又回娘家找她二哥李天增,因他二哥也不经手,也没有找出什么理来,回家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没气死。从那以后不但老太太的高粱没有要出来,还落个老太太拿了他们家大包袱的说法,这件事也是给我爷爷,父亲和老太太娘家产生怨恨的根源。
老太太是何等人物,一星半点的挫折是压不垮他老人家的。他细想此事,也觉得也怨自己怎么就不老早把账和哥哥算一算呢,哥哥死啦和几个侄儿算,他们能承认吗?他们不承认,我这个当姑姑地又能怎么着他们。算了吧,几石粮食呗,我一旦气坏了哪多哪少。想到这。从炕上爬起来,找个自家妯娌拔拔火罐,揪揪脖子,用针扎扎手,打打胳膊,就又重新振作起来,又带领几个儿女拼搏着。
经过几年的拼搏给爷爷、二爷爷、老爷爷都成了家。我爷爷娶的奶奶是大明老赵家的。老爷爷娶的老奶奶姓庞,是西山上的。二爷爷娶的二奶奶是石柱子洼老马家的。一家人现在是其乐无比。这几年又治买了一百多亩土地,盖了十多间房子,又买了一匹白马,日子是过的红红火火。
老太太不但顽强肯干,聪明坚韧。还尊老爱幼,对待老祖宗十分孝顺,在那贫穷,落后黑暗的旧社会,老祖宗竟能活到84岁。那时是人活70古来稀的时代,老祖宗能活到80多岁,这首先就证明了老太太的孝顺。听父亲讲,老祖宗70多岁时就不大出屋了,除一天上两趟厕所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屋里待着。冬天,老太太早晨老早起来做饭时,把火盆给老祖宗生好,端到炕上,把屋子烤暖了,老祖宗才起床。老祖宗的棉袄棉裤哪年老太太都是老早的做的厚厚的,天一冷就让老祖宗穿上。老祖宗的被子,褥子年年拆洗;保证都是干干净,让老祖宗睡的是舒舒服服。那个年代农村根本就没有大米白面,老太太就粗粮细致,给老祖宗做点疙瘩豆(农村的一种面汤),用小米熬点粥,煮几个鸡蛋,蒸碗鸡蛋糕,换着样的侍候老祖爷子,从不惹老祖宗生气。老祖宗能不长寿吗?老祖宗去世那年是1924年的春天,那年父亲李景文都已10岁了。
父亲告诉老祖宗临终时还有个很离奇的故事。
上书交待老太太家不是买了一匹大白马吗。父亲说,那匹马才好呢,个又大,因为饲养的好,胖的像泥垛的似的,活计又好,又体面,老太太都能牵着它拉碾子,拉车,拉犁,秐地样样活都能干,有时还能骑着它上集。
可就这么一匹好马,老祖宗在临终的头一天夜里,老祖宗竟然做了一个梦,他醒来后就召唤爷爷,(因为爷爷和奶奶,父亲和老祖宗住在一个炕上)老祖宗叫着爷爷的小名说:“快起来,快起来,咱们的白马跑了。”爷爷一听,马上起床到马圈观看。看见白马还在石槽上拴着,就回屋说:“爷爷,那马还在圈呢,没跑。”老祖宗说:“跑啦,我看见它顺着大门跑出去啦。”爷爷觉得老祖宗是老糊涂了,也没在意。第二天早晨,爷爷,奶奶老早就起床做饭,爷爷走到马圈前准备给白马添草,发现白马在地上趴着,头扎在地上喘着气,爷爷喊了几声白马也不起来。
骡马没有毛病是不会趴着的,就是睡觉都是站着,一条腿轮换着休息。爷爷见这白马趴着,喊也不起来,就知道有了毛病。就牵着笼头往起拽,强拽起来后,见这白马肚子胀的很大,就牵着到院子遛,遛了半天也不管用。这时听奶奶在屋里喊:“爷爷、爷爷!”原来老祖宗在炕上躺着,奶奶要招呼起来吃饭。可怎么招呼也不见动静,便上前观看,见老祖宗双眼紧闭,嘴角流着口水。这时我爷爷,老太太都听见奶奶在屋没好声地喊,都跑进屋来,看见老祖宗这种情况,老太太对医疗方面也略知一二,便拽过老祖宗的胳膊摸了摸脉,脉都没有了,便对爷爷说:“你爷爷不行啦,快准备后事吧。”这时二爷爷,老爷爷,二奶奶、老奶奶等人也都跑了过来。在老太太的指挥下,七手八脚的把老祖宗从炕上抬起,穿上早已准备好的装老衣裳,全家人无比悲痛。都跪在老祖宗头上嚎啕大哭,左邻右舍,父老乡亲都前来帮忙,从倒座房中抬出早已打好,并找画匠画好的上等棺木,给老祖宗入了殓。忙完了老祖宗的事后,爷爷想起那匹白马。忙走到马圈一看,只见它四腿蹬直,横躺在地上,两眼上翻,早已断了气乡邻们一听这种情况,都说:“这是老祖爷子骑上白马归西去了。”
老太太说:“老祖宗为了这个家操劳了一生,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现在去世了,要好好发送。”就请两伙失亡会,搭上灵棚,又买来一口肥猪,把那匹死去的白马又扒了,伺候乡亲们。上下营子,左邻右舍,亲朋好友100多口大伺候了三天,才把老祖宗安葬。那年是1924年,老祖宗84岁,是上下营子多少年来活的岁数最大的。当年父亲李景文10岁,老祖宗死后,他生前盖的那套被褥,奶奶又拆洗拆洗,给我父亲盖了好几年。父亲说他活的岁数大,与这都有关系。
第二章:父亲一生经历 一、家庭变故
老太太29岁就失去了丈夫,靠自己顽强拼搏艰苦努力,带着四个孩子,把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小家庭,治理成一个有良田二百多亩,房屋二十多间,儿孙满堂的大家庭。
到1937年,全家发展到了二十四口人,老太太有了三方儿媳,十个孙子,三个孙女,两个孙媳妇,一个重孙子。
家庭成员的组成是这样的;上回书中交待,1924年老祖宗去世。现在家中人员是:老太太、爷爷奶奶,二爷爷二奶奶、老爷爷老奶奶,姑奶奶已出嫁,爷爷奶奶生下四个儿子;长子李景耀、次子李景云、三子李景文(我的父亲)四子李景祥。二爷爷二奶奶生下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李景瑞、次子李景龙、三子李景芳,两个女儿不知名字。老爷爷老奶奶生下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李景志、次子李景山、三子李景春、一个女儿不知名字。当年我大爷李景耀也娶上了媳妇,1930年生了个女儿名叫带子,二大爷李景云也结了婚,在1932年生了个儿子名李治国。全家已是四世同堂。小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其乐融融。
我的父亲李景文1914年农历9 月19日出生。当时我们李家没有文化人,奶奶就用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钱,在父亲九岁那年让他上学,念了三年零一冬的私塾。父亲自幼就聪明伶俐,智慧过人。虽然念书时间短,但写文章算账样样精通,毛笔字写得好,算盘打得好,私塾先生非常喜欢他。但因家庭困难,14岁的上半年就被迫辍学,回家务农。那时农民种地也打不多少粮,父亲就觉得靠农业也脱离不了贫困的生活。16岁那年就独自一人去凌源的一个买卖家当学徒。站过栏柜,打过糕点。父亲有文化,心又灵,学的东西又快,买卖家的大掌柜非常喜欢他。但那个社会的剥削阶级的人总舍不得给工人多开工钱,工资很低,父亲在那干了三年就不干了。
当年我爷爷和二爷爷,老爷爷哥三个都在一起过日子,全家二十多口人,在平常没有什么事的时候还能靠种地养家糊口,但有个天灾病业就维持不了生活了。父亲20岁那年和我前一位母亲赵凤贤结婚,我那位母亲的娘家是占巴营子村,广福营子的。婚后三年那位母亲在月子得病去世,生了个女儿也没有活。父亲受到很大的打击。
在那个社会,普通农民家过日子太难了,伪政府的苛捐杂税,地方土匪的欺凌和抢掠,地主老财的欺负,总的讲日子过得很艰难。
1937年的春天,四叔李景瑞,五叔李景志都已订婚,我父亲李景文也和我母亲魏淑珍订了婚。在农历三月初三那天,四叔和五叔哥两个同一天结婚,我父亲和我母亲是1938年春天结的婚。
单说四叔和五叔结婚那天,亲戚朋友都前来祝贺,又顾了两班喇叭匠子,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到了良辰,两对新人都到天地牌位(在正房正门左侧有一天地牌位)前拜堂。我四叔李景瑞身材比较矮,但娶得四婶身材比较高,长得也好看。五叔李景志身材比较高,但娶的五婶是八肯中乡西沟村财主陈老五的姑娘,长得比较俊,但身材比较矮小。(那个年代年青人订亲都是父母包办,不到结婚那天,男女双方互相都不知长的啥样)拜堂时五叔才发现自己的妻子个小。从心里就不太喜欢五婶,所以从结婚那天起就和五婶不对劲,总是不高兴,整天对五婶没有好脸色,而且经常生气。
自古道,‘天遭有雨,人遭有祸,’到了1939年的正月初六。五叔早晨起床时也没有在意,等到老奶奶把早饭都做熟了也不见五婶起床。老奶奶让五叔去叫,五叔没好气的说:“爱起不起咱们吃饭,她不吃拉倒。”老奶奶看儿子不去,便亲自走到儿媳房间,看见儿媳还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就叫了两声,还不见媳妇动弹。便上前推了推,五婶也没反映,也不说话,也不睁眼,这下可吓坏了一家人,便连推带叫的招呼起来。我奶奶和我母亲听见五叔房间中不是好喊,急忙跑了过去,见老奶奶连声招呼:“老五媳妇!老五媳妇!”但五婶就像死过去一样,一动不动,我母亲上前拽过五婶的胳膊摸了摸脉,还在微弱的跳动着,摸一摸鼻子还在喘气,就是什么也不知,胳膊放哪在哪。全家人都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我父亲和我四叔急忙到五婶的娘家报信。五婶的娘家爹陈老五是个私医,家中开着药铺。听见父亲说他女儿得了病,不会说话,一动不动,不懂人事。便随口说道:“我早就知道她们两口子不对劲,准是又生气喝了毒药,去药房拿一副倒药,马上回去给她灌上,我们随后就到。”父亲和四叔到他们药房拿上倒药,一路小跑,回到家中,把药煎好后,几个人七手八脚的给五婶灌上,五婶也没有吐,还是人事不醒。有人又出了主意说让用沙子培,就把毒解啦。这就到河沟内抬来沙子,给五婶培在身上。折腾了一天五婶还是去世啦。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因为西沟陈家是大财主,有钱有势,大小人等来了一百多口,到在我们家中,非打就砸,上房在房顶上压上烧纸,抱一些烧纸和柴在院中点着,一时火光冲天,大哭小叫。把我们家折腾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我父亲见这样下去还得了,马上托人说和。五婶的姥姥家也是老太太的娘家人,父亲就跑到上营子李家找了两位有面子的人出面说和。这样一来,本村的父老乡亲,上营子李家和西沟陈家总计300余口,在我们家大吃大喝,杀猪宰羊,又请来三班失亡会,折腾了七天七夜,老陈家才答应把五婶出殡下葬。下葬时还得扎一处阴宅,父亲也只得满口答应。我父亲又亲自跑到一肯中去买。因为是急用,扎才匠也漫天要价,就扎阴宅就花去小米两石。一切都满足陈家的要求,才被允许把五婶安葬。安葬五婶的棺材是四、五、六寸的,出殡时必须是三十二杠(就是三十二个人来抬)。把五婶抬到坟地,安葬完毕,西沟陈家那一百多口人便直接回西沟去了,父亲请他们到我家吃完饭再走,因为家中都把饭准备好啦,怎么说他们也不肯,便愤然离去。父亲见状也不便强留,便领着一杆人等回到家中,侍候亲朋好友吃完午饭,等亲朋好友散去,家中的爷爷,二爷爷等都坐在一起。父亲对大家说道:“我看西沟陈家今天的表现,中午又没来吃饭,这事肯定还不算完,我们也得有所准备。”当时是二爷爷当家。因为老太太年岁已高,爷爷有时在大明(奶奶在娘家有块地由爷爷奶奶去耕种)所以家里的大事小情就二爷爷管理着。可这次摊上五婶突然死亡这种大事,二爷爷和全家人都束手无策。在这危难之际,父亲站了出来,自己和陈家周旋,又托人说和,又张罗这那,东跑西颠,总算平息了这场灾难。
二爷爷听父亲这么一说,觉得有些道理,便对大家说:“我看老三说的对,(父亲兄弟十人排行老三)陈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会再来找后账。咱们这个家经这么一折腾已不成样子啦,有些事情我也解决不了,我看从今天起,这个家就让老三当吧,早我就看老三有出息,通过这次事,更能说明他有才能,这个家说啥我也不当了,就这么定了吧。”父亲说:“那可不行,这个家还是二叔您来当,有些事情我帮您办就是了。”二爷爷说啥也不当这个家了,非让父亲来当家。
有钱的家好当,五婶一死,陈家这么一折腾,把好好的家折腾穷了,拉了不少外债,这个家怎么当啊。可全家人都一致同意让父亲来当这个穷家。
父亲也考虑到了,什么当家不当家,根据家里这种实际情况,以后的事情都得自己出面解决,还能依靠谁呀。
从那天起,父亲首先处理五婶葬后的善后事宜,被陈家砸烂的东西该修的修,该烧的烧,该扔的扔。有些应用的被砸烂了,就又买的买,没有钱没有粮,就东取西借,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这个破碎的家恢复正常,父亲说那时借的外债连钱带粮合成小米就是二十多石(每石十斗,一斗十升,一石小米大概一千斤左右)。
父亲刚把这个家恢复的有点样子,果然不出父亲所料。五婶娘家爹陈老五托人捎话过来,说他妻子受女儿惨死的打击,得了一场重病,花了不少钱,许让我们赔付,折合成小米要四石米,如果给了还在罢了,如不给就要上告,和我们打官司。
父亲接手当这个穷家,要钱没钱,要粮没粮,陈家又这样苦苦相逼,怎么办,左思右想想起五婶死时,陈家那么折腾,就是这次答应给他们这四石米,以后陈家还不知再出什么妖蛾子,什么坏主意,就不如这次起就回绝他们,看他们到底想咋样。想到这些,就对来人说:“西沟陈家那么有钱有势,还在乎几石小米吗?你也不是不知,老五媳妇的死,都把我们折腾穷了,借了不少的外债,现在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啦,哪还有粮给他们啊,请您回去和陈家好好说说,让他们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又好酒好菜招待来人。来人吃饱喝足,便下地走了。
送走来人,父亲心想,这次没有答应陈家的无礼要求,陈家肯定不会罢休,得有个心理准备,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真不出父亲所料,五婶的娘家爹听来人说父亲没答应他要粮食的要求,心中怨恨。因为西沟陈家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在我们家西南方向居住,和我们家相隔不足两公里。他家有钱有势,据说他们在沈阳有大买卖,家中有田地几千亩。三等院子,四门斗小瓦房,院墙用泥土垛成一米多宽,四米多高,墙顶顿着墙头帽。整个院子足有十几亩地。院子四角盖着炮楼,每个炮楼上都有炮手,枪眼中架着长枪。陈老五的弟弟陈老九念书念到大学,毕业后给日本军当了翻译,成了汉奸。就是这样的一个陈家,在当地可算一霸,没人敢惹。在当地也是说一不二。想整谁就整谁,贫民百姓是敢怒不敢言。陈老五一听说父亲不答应,大怒,第二天骑上他的那匹走马,到小城子警察署找他一个朋友密谋,怎样整治我父亲这一家。并且找人放出话来,说一定要把他女儿的死,让我们李家加倍偿还。
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吃惊。就和爷爷,二爷爷,老爷爷等商议解决办法。但几位老实忠厚的老人和兄弟们都一筹莫展,唉声叹气,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老太太听说啦,也走过来,对父亲说:“老三啊,你快想想办法吧,不然我们都活不下去了。”说着便老泪横流。父亲见状,慌忙上前劝道:“奶奶不必着急,我来想办法就是了”说罢,便把老太太搀到她的屋内。父亲见几位爷爷和叔叔大爷都没有什么办法,就对他们说:“你们也不要着急,急也没用,家里的活计你们干好就行了,这件事就让我来想办法解决吧。”
我的母亲是大城子的娘家,我的舅舅在小城子警察署当警察,父亲想来想去,觉得只能去找舅舅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就亲自走着到小城子警察署找舅舅。因为舅舅就是个小警察,也没什么权力。见父亲找他解决此事,也觉得很为难。他想了想对父亲说:“这件事我也解决不了,不过我们署长曾在我们家住过房,我和他还有些交情,我去找他问一问,但他今天没有来,明天他来了我和他说说看,他要是管,这事就好办,如果他不管,我看这事就不好办了。”父亲觉得就这么空口和署长说,不一定给管,就从衣服兜里掏出些钱来,给舅舅放在桌上,让舅舅买点东西给署长,又详细的把五婶的死和死后老陈家怎么折腾李家,把李家折腾得借了多少外债,老陈家还不依不饶的经过说了一遍。舅舅听后也非常生气,觉得这老陈家做事做的也太过分了。便对父亲说:“你放心吧,这事我一定尽力给你想办法,让署长给你们解决。”父亲听了便千恩万谢的说了不少客气话,这才辞别舅舅回到家中。
第二天,舅舅见警察署长上班了,就去见署长,就把父亲说的,因五婶的死亡,西沟陈家怎么折腾李家,陈家又找人告状的事说给署长听,并把父亲给钱买的东西送给了署长。署长听舅舅这么一说,也觉得这陈家做事太过分,便答应舅舅问一问看陈家找的是谁。
陈老五找的是警察署的一个小官员,当属长问到他此事的时候,他看是署长要管此事,觉得这李家和署长肯定有什么亲属关系,也不好再偏向陈家。便对署长说:“我倒知道此事,但我并没答应给陈家管。”署长又说:“我看这事不能再折腾李家了,我听说都把李家折腾穷了,借了不少外债,现在一家二十几口人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也就行了,再说他的女儿说不定是怎么死的,有可能是得了急病死的。我看你就不要管了。”那个小头目急忙点头答应。
又过了几天陈老五又去小城子找那个小头目。小头目对陈老五说:“这个事我不好管了,警察署长插手了,警察署长和李家可能是亲属。我看你在这是告不成了,你要告就到平泉去告吧。”陈老五一听这李家和署长是亲属,就是到平泉去告也未必能赢。再说平泉路途遥远,又没有认识人,这才作罢。
老陈家的事平息后全家老老少少都松了口气,左邻右舍也觉得父亲年纪轻轻的,把当地有名的大财主找茬的事都给摆平了,都对父亲刮目相看。
平息了陈家的事,父亲就和我三位爷爷,几个叔叔大爷齐心协力的奋斗着。
但是,褔不双至,祸不单行。这一年刚刚收完秋,老太太又病倒了。老太太毕竟是75岁高龄,又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吃苦受累。正月又死了五孙媳妇,陈家又打又砸,老太太再也经受不住了,就一病不起。父亲多方请医用药,但都不见好转。老太太在病床上躺了半年。于1940年的三月与世长辞,享年76岁。
老太太去世了,老太太娘家来了很多人,父亲的二舅爷李天增对我爷爷说:“大外甥,你妈29岁守寡,拉扯你们几个,一辈子不容易啊,现在老啦,得好好发送一下呀!”我爷爷老实忠厚,又觉得他二舅说的有道理,随口就答应了。就叫父亲张罗此事,爷爷不当家,对家里的情况了解不清。但父亲知道,全家二十多口人吃饭的问题都难以解决,欠下这么多外债,怎么张罗啊。但爷爷都答应了,也不好回绝。就东取西借。当时家中虽然贫穷,但亲朋好友都信任父亲,都上赶着借给我们。父亲又派人到瓦房赊来二十领炕席,搭了一个好大的灵棚。又赊来两口肥猪,又借来一石小米。老太太娘家大人孩子就来了近百人,再加上东邻西舍,亲朋好友总计近二百人。又请了两班失亡会,吹吹打打,大吃大喝支应了三天,才安葬了老太太。
这样家里就债台高筑。爷爷和他两个兄弟就无法在一起生活下去,就商量着分开过。父亲把一年来的账本拿出来,借哪个亲属多少钱,那个朋友多少米,都记得清清楚楚。按当时的粮价,把钱都合成米,总计欠外债二十四石七斗小米。按三份分,每家分八石多米的外债,父亲说:“你们两家每家分八石米的外债,剩下的八石七斗米外债由我承担。”箱箱柜柜先记着二爷爷,老爷爷他们两家挑,剩下的父亲再要。房子和房身,二爷爷要前院的东西两院,老爷爷要西院和场院,我们要老院。分家时土地总计是210多亩,长条子地,头节地等平整的土地先让二爷爷和老爷爷挑,南洼子二十二亩薄地,南北垄又顺水谁都不愿要,父亲就自己留下,东洼的地倒是平整,但离家太远,又挨着石柱子洼,梁东,哪年庄稼熟了,都得没黑带白的看着,那有时还丢。二爷爷和老爷爷他们也不愿要,父亲说了:“你们不必多想,你们想要那块地就要哪块地,剩下的地我再要。”就这样好一点的地让给二爷爷,老爷爷,剩下的地是父亲这家的。就这样,就把一个有20多口人的大家庭分成了三家。现在还存分家单在45页。
编后语:关于《《前辈的人生》: 艰贞的老太太》关于知识就介绍到这里,希望本站内容能让您有所收获,如有疑问可跟帖留言,值班小编第一时间回复。 下一篇内容是有关《《看我召唤出了什么》免费试读_云游尸人》,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进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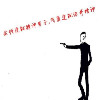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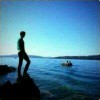


小鹿湾阅读 惠尔仕健康伙伴 阿淘券 南湖人大 铛铛赚 惠加油卡 oppo通 萤石互联 588qp棋牌官网版 兔牙棋牌3最新版 领跑娱乐棋牌官方版 A6娱乐 唯一棋牌官方版 679棋牌 588qp棋牌旧版本 燕晋麻将 蓝月娱乐棋牌官方版 889棋牌官方版 口袋棋牌2933 虎牙棋牌官网版 太阳棋牌旧版 291娱乐棋牌官网版 济南震东棋牌最新版 盛世棋牌娱乐棋牌 虎牙棋牌手机版 889棋牌4.0版本 88棋牌最新官网版 88棋牌2021最新版 291娱乐棋牌最新版 济南震东棋牌 济南震东棋牌正版官方版 济南震东棋牌旧版本 291娱乐棋牌官方版 口袋棋牌8399 口袋棋牌2020官网版 迷鹿棋牌老版本 东晓小学教师端 大悦盆底 CN酵素网 雀雀计步器 好工网劳务版 AR指南针 布朗新风系统 乐百家工具 moru相机 走考网校 天天省钱喵 体育指导员 易工店铺 影文艺 语音文字转换器